走向重新思考托洛茨基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地位
作者:大卫·诺斯
2013年4月10日
本文是世界社会主义网站编辑部主席和美国社会主义平等党全国主席大卫·诺斯2001年1月21日在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平等党在悉尼主办的国际学校的演讲。这是演讲的修订文本,收录在大卫 • 诺斯的《捍卫列昂·托洛茨基》一书里。
* * *
六十年前的1940年8月21日,托洛茨基因苏联秘密警察的特务前一天所造成的重伤而去世。斯大林主义政权期望这次谋杀不仅会使它最大的对手及其政治活动完结,而且还要消灭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极权的实用主义算计被证明是短视的。凶手结束了托洛茨基的生命。但是这位伟大革命家的思想与著作继续活着。杀害托洛茨基并没有终结他所创立的世界运动的政治工作。事实证明,第四国际不仅活着,而且还见证了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崩溃。同样地,那次暗杀当然也没能把托洛茨基从历史中除去。当历史学家们研究及阐释二十世纪时,托洛茨基这位人物将会显现得越来越高大。只有很少人的一生能像托洛茨基这样如此深远和崇高地将上个世纪的斗争、抱负及悲剧反映出来。如果我们认同托马斯 • 曼的观察,“在我们的时代,人类的命运在政治术语中表达出意义”,那么我们可以说,在托洛茨基60年的生命里,命运得到了最充分的实现。托洛茨基的生平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之沧桑的集中表达。
托洛茨基于逝世前三年,与一个带着怀疑态度的美国记者讨论时解释道,他不把自己的一生看作一连串扑朔迷离,并最终是悲剧性的经历,而是革命运动的历史轨迹的不同阶段。他在1917年上台掌权是工人阶级革命高涨的结果。在六年里,他的权力取决于那场进攻所创造出来的社会和政治关系。托洛茨基个人政治命运的下降,则是由于革命浪潮的消退。托洛茨基丧失了权力,并非因为他是一个比斯大林技巧更差的政治家,而是因为他的权力所依凭的社会力量——即俄国和国际工人阶级——正在作政治的退却。的确,托洛茨基对政治的历史意识在革命年代是如此行之有效,在政治日益保守的时期,相对于肆无忌惮的对手,却使他处于不利的地位。俄国工人阶级在内战后精疲力竭,苏联官僚体制政治势力的不断膨胀,欧洲特别是德国的工人阶级屡遭失败,这些都最终导致了托洛茨基的下台。
国际工人阶级的失败都记载在托洛茨基个人的命运当中:1927年中国革命的失败引起的政治消沉给予斯大林一个好机会,从共产国际开除左翼反对派,并且放逐了托洛茨基——首先到阿拉木图,然后不久便到苏联的边界以外。希特勒在1933年的胜利——由斯大林集团所领导的德国共产党的政策所造成——推动了一连串的事件,以“莫斯科审判”和斯大林的人民阵线主义的政治大灾难为高潮,最终使托洛茨基从欧洲被放逐到遥远的墨西哥。
正是在墨西哥市的一个区科约阿坎,托洛茨基被斯大林的特务拉蒙 • 梅卡德尔杀害。托洛茨基的死,正值法西斯和斯大林集团的反革命高峰。到1940年时,几乎所有托洛茨基在苏联的老同志已遭清算。托洛茨基死了四个孩子。两个大女儿因为父亲被迫害所造成的艰辛环境而夭折。两个儿子,萨其与列夫是被斯大林政权谋杀的。在列夫 • 谢多夫于1938年2月在巴黎被杀害时,是除了他父亲之外第四国际里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其他第四国际秘书处的著名人物,如欧文 • 沃尔夫和鲁道夫 • 克里门特,分别在1937年及1938被刺身亡。
到1940年时,托洛茨基认为他自己被暗杀将是不可避免的。这并不意味着他无奈地接受命运。他做了一切力所能及的,去延迟斯大林及其人民内务部机构的特务所准备的袭击。然而他明白,斯大林的行动由是苏联官僚的需要所决定的。“我活在世上,”他写道,“不是因为合乎规则,而是一种例外。” 他预测斯大林将会在1940年春夏时利用西欧爆发大战的机会进行袭击。托洛茨基被证明是正确的。
第一次严重的暗杀发生在1940年5月24日晚上,当时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希特勒击溃法国军队上。第二次亦是成功的行刺,发生在同年夏末的不列颠战役期间。
为什么要惧怕流亡国外,而且看来是孤立的托洛茨基呢?为什么斯大林认为他的死是如此必要呢?托洛茨基自己提供了一个政治上的解释。1939年秋,在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了条约(他也早已预料到的)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数周后,托洛茨基注意到巴黎一份报张所报道的希特勒和法国大使罗伯特 • 高伦第之间的谈活。正当希特勒吹嘘他与斯大林的条约,将使他能腾出手来,在西线击败德国的敌人,高伦第立刻打断元首,警告说:“真正的胜利者(如果发生战争的话)将是托洛茨基。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一点?” 希特勒表示同意法国大使的看法,但指责是他的对手迫使他这样做。托洛茨基引用这个惊人的报道,写道:“这些先生们想用一个人的名字来命名革命的幽灵...... 高伦第和希特勒两人都代表了正在欧洲前进的野蛮主义。两人都毫不怀疑,他们的野蛮行动将被社会主义革命所征服。”
斯大林也没有忘记,俄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遭受到的失败,使沙皇政权声誉扫地,从而引发群众的运动。尽管他与希特勒有了协议,可是一旦战争再次爆发,难道不存在着类似的危险吗?只要托洛茨基仍然活着,他就仍然是官僚独裁政权的伟大的革命替代者,仍然是1917年十月革命的纲领、理想和精神的体现。这就是托洛茨基被行刺的原因。
但即使在逝世后,对托洛茨基的恐惧仍没有减弱。很难想象还会有另一个人不仅在生前甚至在死后几十年,仍能保持使当权者惧怕的力量。托洛茨基的历史遗产抗拒任何形式的同化与拉拢。马克思去世不到十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们已经找到办法,改造他的著作使其适应于社会改良的观点。列宁的命运更是可怕,他的遗体被防腐处理,他的理论遗产被歪曲,被改造为官僚认可的国家宗教。但对托洛茨基,这已经证明是不可能的。他的著作和行动的革命内涵实在是太精确了。此外,托洛茨基所分析的政治问题,他所定义的社会政治关系,甚至他恰如其份和苛刻地描画的各政党的特点,仍在本世纪余下的时期持续地应验。
1991年,杜克大学出版了罗伯特 • 亚历山大的一份一千多页的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研究报告。亚历山大在序言里评论道:
直到二十世纪80年代末,托洛茨基主义者从来没有在任何国家上台掌权。虽然国际托派不曾享有一个稳固政权的支持,如斯大林主义的继承者那样,然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世界许多国家中的持久性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政治生活的不稳定性意味着,不能完全在可预见的未来排除托洛茨基主义政党上台的可能。
亚历山大的书出版后不久,那个“稳固的政权”便消失了。苏联官僚从来没有给托洛茨基平反。经常有人指出历史是最伟大的讽刺家。数十年来,斯大林集团声称,托洛茨基企图毁灭苏联,更曾参与帝国主义试图肢解苏联的阴谋。因为这些指控,托洛茨基被苏联当局判处缺席死刑。然而最终却是,正如托洛茨基所预警的,正是这个苏联官僚自己把苏联消灭了。而官僚在这样做时,也没有坦率公开地否定对托洛茨基和他的儿子列夫 • 谢多夫的指控。相反,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而言,签署对苏联执行死刑的命令,比承认对托洛茨基的一切指控全是假的,更为容易。
尽管过去的60年里发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变迁,我们与托洛茨基所面对过的问题、课题和主题并不遥远。即使在苏联瓦解后,托洛茨基的著作仍是异乎寻常地保留着与当代密切的相关性。研究托洛茨基的著作,不仅对了解二十世纪的政治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对我们在二十一世纪非常复杂的世界上确定我们的政治方向,也同样重要。
如果一个政治人物的伟大是以他的遗产的广大和持久相关性来衡量的话,那么托洛茨基必须被置于二十世纪领袖的前列。让我们回顾一下在1940年时支配世界舞台的政治人物。提及那个时代的极权主义领袖的名字,如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和佛朗哥,不用难听的话,一定是很困难的。除了罄竹难书的罪行,他们身后什么也没有留下。至于帝国主义民主国家的“伟大”领导人如罗斯福或丘吉尔,没有人会否认他们个性鲜明而且显示了在常规的议会政治框架内的技巧。丘吉尔比那美国总统更为辉煌,他是一位天才的演说家,也表现出一定的作家技巧。然而这两人能谈得上有什么遗产吗?丘吉尔对衰落的大英帝国的歌颂甚至被许多崇拜者认为不合时宜。他的著作只有作为历史文献的吸引力,却很难与当代相关。罗斯福无疑是个精湛的政治实用主义者,能结合狡诈和直觉来应付当时面对的问题。然而我们真的可以从丘吉尔或罗斯福的讲话或著作中(顺便说一句,后者没有任何著作)找到有用的分析和见解,来帮助我们理解刚开始的二十一世纪的政治问题吗?
即使在他们的时代,托洛茨基在政治同辈中也是鹤立鸡群的。所有他的对手的影响力,都源于他们直接倚赖和掌控的国家权力机构。假如他们离开了权力,则难以吸引世界的注意。离开克里姆林宫及其恐怖机器,斯大林就只不过是1917年10月之前的他: “一团模糊的灰色。”
在1927年,托洛茨基被剥夺了一切官方权力。然而,他从来都不是没有权威的。托洛茨基很喜欢引用易卜生的《人民公敌》中斯托克曼医生讲的著名结尾句:“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正是最孤立的人。” 伟大的挪威剧作家的洞察力,在俄国最伟大的革命家的生命里得到了实现。托洛茨基为那些符合和促进人类进步而奋斗的思想和理想的威力提供了一个永恒的范例。
作为作家的托洛茨基
当谈及托洛茨基的思想时,是很难抵挡大量地引用他的著作的诱惑的。至少人们必定会为听众提供一种优秀的审美体验。让我们暂时撇开个人的政治倾向,任何有客观判断能力的读者都难以否认,托洛茨基可以跻身于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行列。我第一次读到托洛茨基的不朽著作《俄国革命史》已是30年前的事了。我相信除我之外还有很多人仍能记得第一次与托洛茨基那令人惊讶的散文相遇时所造成的情感和理智上的震荡。当我阅读托洛茨基的翻译本时,我想知道那些能够读懂俄文原著的,会怎样评价他作为作家的地位呢。没想到,满足我的好奇心的机会来了。我参加过一位在十月革命后逃离祖国的年迈的俄罗斯文学专家的讲座。他并非是一个你能期望会对托洛茨基有丝毫同情心的人。在他的关于二十世纪俄国文学概述的演讲完结后,我问他对托洛茨基作为一个作家的评价。我清楚地记得他浓重的口音和有力的回答。“托洛茨基,” 他答道,“是托尔斯泰之后俄国最伟大的散文大师。” 许多年后,当我于1989年第一次游历苏联时,这种评估回荡在我所遇见到的一个学生的评价中。他坦言,阅读托洛茨基对他来说是一种非常困难的经验。为什么会这样呢?“当我阅读托洛茨基时,” 他解释说,“我不得不同意他的说法,可是我却不想!”
托洛茨基作品的范围广泛,包括艺术、文学与文化、科学发展、生活问题,当然还有政治,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们这些只有普通天资可用的凡人,只能惊叹于托洛茨基的文献产量。我们会自问,在微软文字处理和拼写检查的时代之前,他怎么可能做得到呢? 也许部分的答案在于托洛茨基非凡的、即席讲话的能力,他说的与他写的是同样美妙及有说服力。一致的说法是,他的即席口述比很熟练的作家修饰过的草稿还好。
作为二十世纪文献的一个重要人物,托洛茨基极大地受益于十九世纪的俄国大文豪,特别是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赫尔岑和别林斯基。他既能书写顽强不屈的军事宣言和战场命令,激励起数以百万的人,也能写作难以忘怀的美丽章节。例如当他回忆起在1907年从西伯利亚流放地逃脱的那一刻:
雪橇悄无声息地像只船一样沿着池塘的玻璃面顺畅滑行,在渐浓的暮色下,森林看上去好像比以前更加葱茏。我看不到路,一点儿也感觉不到雪橇正在移动着。树木仿佛像着了魔般朝我这边跑来,灌木溜走了,覆盖着积雪的残树树桩飞过去了,一切似乎都是神秘的。只有那急速的、有规律的驯鹿的低声呼吸...... 雪...... 雪...... 雪。数以千计早已忘怀的声音在沉默中充满了我的脑袋。突然间,我听到了从黑暗森林的深处隐隐传来汽笛的尖叫声,似乎很神秘,无限地遥远。然而,这只不过是我们的奥斯也其向驯鹿发号施令。之后再度沉默,更遥远的呼啸,更多的树悄无声息地从黑暗冲向黑暗。
托洛茨基对政治上的难题与矛盾是非常敏锐的。托洛茨基书写自己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受审时,描述了挤满“上了刺刀的宪兵”的法院大楼及其严峻与威吓的官方环境,以此来对比仰慕和支持革命被告人而被送到审判室的“无数的花卉”:
钮扣上的花,手提着的花或放在膝上的花,还有干脆放在凳子上的花。法院院长不敢除去这些芬芳的闯入者。最后甚至连宪兵、军官们以及法院职员,全部都十分沮丧,只好把鲜花交给被告。
我相信,像作家萧伯纳曾察觉到,当托洛茨基用自己的笔割去了对手的头时,他难以舍弃这个机会,把它捡起来让所有人看看,里面是沒有脑袋的。然而,托洛茨基的论战才华,在于他能超卓地指出这个或那个政治家的主观目的是与革命时代的社会矛盾和客观发展不协调的。托洛茨基用历史过程的必然发展作为参照准则,他的尖刻批评并非是无情的。它们只是一语中的。故此,有关1917年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首要领导人,他写道:
克伦斯基不是一个革命家,他只不过在革命外边徘徊...... 他沒有理论准备,沒有政治训练,沒有思考能力,也沒有政治意志。取而代之的是容易受人影响,性情暴躁,还有那种不能影响人的思想及意志,而只能刺激人们神经的口才。
至于社会革命党的领导人维克多 • 切尔诺夫:
与其说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毋宁说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他具有相当的学识,但不能将这些知识融会贯通。切尔诺夫常能漫无止境地引经据典,借以作适当的辩解,长期以来这种才能吸引了不少俄国年青人,却没有教导他们什么。可是,这个多言的领导人却独有一个问题他没法回答:他在领导谁,以及领导他们向何处走?切尔诺夫的折衷主义公式是用道德准则和诗句装饰起来的,在一定的时间内能够将各式各样的群众结合在一起,但一到紧急关头,他们就向不同方向散去了。难怪切尔诺夫自满地以他的建党方法来对比列宁的“宗派主义”。
最后,关于曾经令人敬畏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
考茨基有一条清楚和单一的得救道路:民主。这就是全部的需要,每个人都应该承认这一点并将自己与它捆绑在一起。社会党的右派必须摈弃他们为执行资产阶级的意志所进行的血腥屠杀。资产阶级本身则必须放弃利用诺斯克们和沃格尔中尉们去捍卫其特权至最后一口气的观点。最后,无产阶级必须一劳永逸地拒绝通过宪法规定以外的方法去推翻资产阶级。如果所列举的条件得以遵守,则社会革命将会毫无痛楚地融入于民主之中。为了取得成功,我们只需把一顶睡帽盖在狂风暴雨般的历史头上,然后从考茨基的鼻烟盒中取出少许的智慧。
人们能轻易地用一整天来引用托洛茨基这位文学天才所表达的杰出章节。但这天才却不仅仅是,也主要不是风格的问题。这里有更深层和更深刻的原因使托洛茨基的文献高于任何同期的政治思想家。在某种程度上,历史自身对当前展开过程的自觉表达,就体现于托洛茨基的著作中。一般来说,没有什么文章,会比政治评论更为短暂。即使是写得很好的报纸专栏,其生命周期一般是不超过喝一杯咖啡的时间,然后它便直接从早餐桌上丢到字纸篓去了。
托洛茨基的著作却非如此,我所指的不单是他的主要作品,还包括他在报章上的评论。而且我必须补充,这还包括托洛茨基的演说。列昂 • 托洛茨基的著作和演说经常代表了历史第一次尽力尝试去解释它在试图做些什么。托洛茨基最伟大的政治著作的目的是从世界历史的轨迹上找出社会主义革命最新发生的事件,这些反映在他所选的标题如《我们经历过什么阶段?》、《英国往何处去?》、《法国往何处去?》、《走向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等。
卢那察尔斯基曾经这样谈及托洛茨基:他总能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这就是托洛茨基对抗机会主义与各种压力的力量泉源。托洛茨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思考方法的科学”。
斯大林主义对革命干部的摧残,及侵蚀作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理论武器的马克思主义的后果,便是庆贺出现了各类与这个斗争互不相关的所谓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美学家等。然而,当他们试图运用其掌握的所谓辩证法来分析当时的政治事件时,便立刻被证明是不能胜任的。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学派里,托洛茨基是一个让我们把它称之为经典学派的最后一位伟大的代表人物,这个学派对辩证法的掌握的最重要体现是能够评估政治局势,提出政治展望,并且制定战略方向。
重新评估托洛茨基
第四国际在其历史中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便是要捍卫托洛茨基的历史角色,对抗斯大林主义的诽谤。这项工作捍卫的不只是个人,也是捍卫国际马克思主义与十月革命的整个纲领性的传统。第四国际在捍卫托洛茨基时,维护了历史的真相,坚持反对篡改与背叛布尔什维克革命所依据的原则。
然而,尽管第四国际坚定地维护托洛茨基,它有没有公正地对待这位“老祖宗”的政治和历史遗产呢?托洛茨基活着的世纪已经过去了,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更加丰富地和深刻地理解他的政治遗产和历史地位是可能的。让我们开始这个工作,批判地再次思考以下众所周知关于托洛茨基评估自己对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的贡献的一段话。
1935年3月25日,托洛茨基在他的日记写道:
假如在1917年我不在圣彼得堡,十月革命仍然会发生,但条件是列宁在场指挥着。假如列宁与我都不在彼得堡,则十月革命便不会发生: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会阻止革命成事,我丝毫没有对此怀疑过! 假如列宁不在彼得堡,我怀疑我能否有能力去克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阻力。对抗 “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即无产阶级革命)便早在1917年5月时已开始了,因而革命的结果将难料。但我重申,因为列宁是在场,所以十月革命无论如何都会胜利的。大体上来说,内战也一样,虽然在第一阶段,特别是当喀山与辛比尔斯克沦陷时,列宁曾经动摇过,因怀疑而有所困扰。但是,这无疑是一个短暂的心情,除了我他甚至可能从没有对任何人承认过...... 故此我不能说我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这甚至包括我从1917年到1921年期间的工作。
这评估是准确的吗?在这段话里,托洛茨基主要是指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政治斗争。他相当正确的以1917年4月布尔什维克党重新确定方向的关键意义为出发点。列宁使1917年革命成功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克服了老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阻力,尤其是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从而在战略上改变了布尔什维克的政策。
然而,布尔什维克党内的这场重要的斗争,只是更突现了早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关于政治观点问题的争议的深远意义。即使人们承认列宁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克服了布尔什维克党内的阻力,采取了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事实上列宁发动斗争反对的那些人所遵循的政治路线,正是他本人曾经坚持多年的反对托洛茨基的观点。
当列宁在1917年4月返回到俄国,摈弃了“工农民主专政”的观点后,当时的广泛理解是他采纳了——即使他没有公开承认这一点——与托洛茨基相联十多年的政治路线,即不断革命论。
不断革命论
我将会简单回顾一下在沙皇政权的最后数十年,俄国革命运动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俄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在预测俄国社会政治发展轨迹方面的努力方面,提出过三种互相冲突的可能版本。有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称号的普列汉诺夫,设想俄国社会发展是一种形式逻辑的进程,其历史发展阶段是由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正如封建主义被资本主义所取代那样,当一切必需的经济发展条件已具备时,后者反过来,将让位于社会主义。普列汉诺夫所研究的理论模型,是假设俄国的发展将会遵循西欧资产阶级民主演进的历史模式。他认为俄国比更为先进的西方国家更早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在二十世纪之交时,普列汉诺夫认为,俄国仍然要面对实现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他所指的是推翻沙皇政权,为未来而遥远的社会革命创造政治与经济的先决条件。俄罗斯很可能要面对的是几十年的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发展,然后它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才可承受社会主义的改造。这种俄国发展的形式概念便成为了在二十世纪初年,广泛地盛行于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公认观念。然而,普列汉诺夫的立场有一个不能解决的矛盾,正反映出俄国社会发展的特有性质。早在1889年,普列汉诺夫便曾预见,俄国工人阶级会在将要来临的革命,发挥领导作用。在创建第二国际的大会上,他宣言俄国革命只有以工人革命才能成功。然而,这种见解如何能够与坚持在革命之后,政权要由俄国资产阶级来掌握的观点调和起来呢?普列汉诺夫在这个问题上始终未能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回答。
1905年的事件——即第一次俄国革命的爆发——对普列汉诺夫的理论模式提出了严重的质疑。俄国革命最重大的意义,是在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中,无产阶级扮演了主导的政治角色。在总罢工和起义的背景下,投机的俄国资产阶级政治领导人表现出的是卑鄙和欺诈。资产阶级当中找不到罗伯斯庇尔或丹东。立宪民主党亦未曾与雅各宾党人有相似之处。
列宁的分析比普列汉诺夫更进一步和更为深刻。前者接受了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但是这样的定义,并不能彻底地解决革命中各阶级力量的关系和权力分配的问题。列宁坚持工人阶级的任务是通过其独立的组织和努力,争取最广泛和最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也就是说,进行一场毫不妥协的斗争,摧毁一切沙皇封建主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痕迹;从而创造最有利的条件,为俄国工人运动的兴盛,建立一个真正进步的、宪制民主框架。对列宁而言,“土地问题”的解决正是民主革命的核心问题——他所指的是破坏所有封建主义的经济和法律的残余。贵族的大土地占有权构成了对俄国生活民主化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
相比于普列汉诺夫,列宁所构想的资产阶级革命并没有被形式主义的政治偏见所局限。可以这样说,他是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内部去理解问题的。列宁不是从一个形式的政治图式出发——即资产阶级革命必然的结果就是议会民主——而是试图从革命的核心社会内容来推导出其政治的形式。
与普列汉诺夫相反,认识到即将来临的俄国民主革命包含巨大社会任务的列宁认为,它的成功在俄国资产阶级的政治领导下是不可能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工人阶级进行独立于,并且事实上,反对资产阶级的民主斗争,才有胜利的可能。但由于数量上的弱势,民主革命的群众基础无法仅由工人阶级提供。俄国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毫不妥协地推动土地问题的激进和民主的解决,以动员起亿万俄国农民的支持。
那么,从这两大群众阶级的革命联盟中产生出来的国家政权形式是如何的呢?列宁提出新的政权将会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实际上,这两个阶级将分享国家权力,并在它们共同主持下,最大可能的实现民主革命。但列宁却没有给如何在这种政权内安排和分享权力提供细节,他也没有界定和说明这种两个阶级专政使用的国家形式。
尽管民主专政在政治上是激进的,但列宁仍然坚持它的目的并不是沿着社会主义路线去改造社会经济。相反,就经济纲领而言,革命仍必然是资本主义的。实际上,即使列宁主张激进地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即针对俄国大庄园的土地国有化,他强调这乃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的措施。
列宁在他的论战中,在这一关键点上并没有动摇过。在1905年他写道:
马克思主义者绝对相信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那些对俄国来说是势在必行的...... 民主改革...... 就其本身来说,不仅不会摧毁资本主义,不仅不会摧毁资产阶级的统治,反而会第一次为资本主义的广泛而迅速的发展,即欧洲式的而不是亚洲式的发展,真正扫清基地,第一次使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统治成为可能。
托洛茨基的立场与列宁和孟什维克有极大的不同。尽管普列汉诺夫与列宁有不同的结论,他们的观点都是基于对俄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以及国内现有社会力量关系的评估。但是托洛茨基的真正出发点,并非是俄国现有的经济水平,或者它内部的阶级力量的关系,而是俄罗斯迟来的民主革命注定展开的世界历史环境。
托洛茨基探索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轨迹,从十八世纪时的古典形式,经过十九世纪的变迁,而终于1905年的现代背景。他解释在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工人阶级的出现,如何改变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社会和政治动态。因此在新的形势下,以十九世纪中叶盛行的条件为基础的传统政治方程式,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托洛茨基发现列宁的政治公式有其局限性。在政治上它不切实际:它回避了国家政权的问题。托洛茨基不接受俄国无产阶级会在形式上把自己局限于民主性质的措施。现实的阶级关系将迫使工人阶级行使其政治专政反对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换言之,工人阶级的斗争会必然地呈现出社会主义性质。但鉴于俄国的落后性,这又怎么可能呢,因为俄罗斯自身经济发展的局限性显然没有为社会主义准备好。
若只从俄国革命内部看,这个问题似乎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但如果从世界历史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国际发展的制高点来观看,则会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解决方法。早在1905年6月,托洛茨基便指出“资本主义已经把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政治和经济有机体”。托洛茨基抓住了这个世界经济结构的改变的含意:
这就使当前形势的发展从一开始就立即具有国际性,并打开了一个广阔的视野。俄国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政治解放,将会把这个领导阶级的地位提到历史上空前的高度,它将掌握巨大的力量和资源,使它成为消灭世界资本主义的启动者,因为历史已经为资本主义的消灭创造了一切客观条件。
托洛茨基的探讨方法代表了一次关键性的理论突破。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怎样去分析革命过程的角度。1905年之前,革命的发展被视为一个国家的一系列事件,其结果是由国内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关系的逻辑所决定。托洛茨基提出了另一种方法:把现代革命的实质理解为从政治上植根于民族国家的阶级社会,过渡到以经济全球一体化和人类的国际统一为基础的无阶级社会的一个世界历史性的社会进程。
托洛茨基发展出这个革命进程的概念时,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着大量社会经济和政治数据,不能在现有的理论框架内作合理的分析。仅是现代世界经济的复杂性就违反了旧的形式定义。世界经济的发展对每个国民经济的外貌的冲击在那时是前所未有的。即使在落后的经济体里——由于国际对外投资的结果——同样能找到非常先进的特征。在某些封建或半封建政权,其政治结构仍被中世纪残余的硬壳所覆盖,它们却主持着一个以重工业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在一个资本主义发展迟来的国家,资产阶级对“自己的”民主革命的成功的兴趣,还不及本国工人阶级,也不是不寻常的事。这种反常现象无法与形式主义的战略信条调和,因为这种估计假设现存的社会现象是较少被内在矛盾所撕裂。
托洛茨基的伟大成就在于为现代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复杂性,阐明了一个新的理论架构。托洛茨基的探讨方法完全不是空想。更确切地讲,它代表一种对世界经济对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影响的深刻洞察力。只有在把国际放在民族性之上作为客观出发点,社会主义政党才有可能采取现实的政治立场和有效的革命战略。但这并不简单地意味着推广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如果不了解其在世界经济中实质和客观的基础,如果不把世界经济的现实作为战略思想的根基,那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只能停留于乌托邦的空想中,并与立足于各民族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的纲领和实践毫不相关。
托洛茨基以分析世界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与俄国所客观依赖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为出发点,预见到俄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俄国工人阶级将被迫夺取政权并采取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然而,在沿着社会主义路线前进时,俄国工人阶级不可避免地碰到民族环境的局限。它如何从困境中寻找出路呢?把它的命运与欧洲和世界革命联系起来,因为归根到底,它自身的斗争只是世界革命的一个表现。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使世界革命有可能成为现实概念。民族革命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民族革命只能从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框架内才能加以理解。
托洛茨基与布尔什维克
只有当我们思考托洛茨基分析的含意时,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他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分歧。我不打算在这里以任何方式贬低列宁的伟大成就,他比任何人都更为深刻地理解在革命运动中反对政治机会主义,并把这种斗争扩大到党的工作和组织的每个方面的政治意义。然而,无论革命组织的问题是如何重要和关键,二十世纪的经验已经教育了工人阶级,或者说,应该教育了工人阶级,即使是最坚定的组织,除非以正确的革命观点为指导,最终它亦有可能成为革命的障碍。
对托洛茨基而言,决定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劳工运动内所有倾向的,就是他们的观点和纲领。托洛茨基的问题是,在何种程度上他们的政治纲领是基于将要决定俄国革命的发展与命运的世界力量的正确评估呢? 托洛茨基从这个角度出发,合乎情理地批判布尔什维克的纲领和观点。让我们读一读他在1909年所写的一篇他调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不同派别所持有的不同立场的文章。托洛茨基写道:
列宁相信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客观条件之间的矛盾将会得到解决,因为无产阶级会在政治上约束自己,而这种自我限制来自无产阶级的理论觉悟,那就是它扮演领导角色的革命乃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列宁把客观矛盾转移到无产阶级的意识里,并用阶级禁欲主义来解决这个矛盾,这不是基于宗教信仰,而是一个所谓“科学”纲要。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个理论的构建,是多么彻底的唯心主义。
...... 问题是布尔什维克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想像只到革命胜利时为止,然后他们便把阶级斗争暂时地溶入“民主”联盟里面,再以纯粹的形式出现——这次是直接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了——但是只在共和制明确建立之后。鉴于孟什维克是从抽象概念出发,认为“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因而得出无产阶级必须使其所有的策略去适应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行动,以确保将国家政权移交给资产阶级,布尔什维克则从同样抽像的概念出发——即“民主专政而不是社会主义专政”——因而得出无产阶级拥有了国家政权,却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局限强加于自身的想法。诚然,在这个问题上它们之间的差异是相当大的:虽然孟什维主义的反革命特征已经是很明显,而布尔什维克的反革命特征却仅仅在胜利的情况下,才可能成为严重的威胁。
这是一个有先见之明的洞察,因为俄国革命实际上就是这样发生的。一旦沙皇政权被推翻后,列宁的民主专政观点的局限性便立即凸显出来。托洛茨基接着说,俄国工人阶级将被迫夺取政权,并“将会面临社会主义的客观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碍于国家的经济落后,这些问题将得不到解决。这个矛盾在民族革命框架里是没有出路的。” 因此托洛茨基意识到列宁观点的局限性不仅在于他的政治估量,更因为这种政治估量是从民族的框架,而不是从理解俄国革命将要展开的国际框架出发。
托洛茨基继续写道:
工人政府一开始将面临的任务,就是将自己的力量与西欧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只有这样,临时的革命支配权才能成为社会主义专政的前奏。因此,对俄国无产阶级来说,不断革命将会成为阶级自我保存的问题。如果工人政党不能为积极的革命策略表现出足够主动性的话,如果它还把自己的专政节衣缩食,仅仅局限于民族的与民主的,那么欧洲联合起来的反动势力将马上向工人阶级表明,只要它拥有了政权,就必须全力以赴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
这是一个核心问题。对国家政权形式的评估,来自于对决定革命运动的政治后果的国际因素的不同估量。在评估布尔什维克党的发展时,必须考虑以下一点。每个纲领都反映了社会力量的利益和影响。在资产阶级发展滞后的国家,资产阶级不能坚定地维护民族民主革命的职责,这些任务的基本要素便构成了工人阶级纲领的组成部分。工人阶级必须继承那些仍有进步意义的民主和民族要求。在二十世纪有很多场合中,社会主义运动被迫承担起这些民主和民族责任,从而在队伍里吸纳了将这些当成是首要任务的份子——对他们而言,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抱负是次要的。民族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倾向的混合大大影响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发展。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框架内,列宁无疑代表了反对这种民族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民主偏见的最坚决的力量。他知道它们的存在,并且无法忽略它们。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1914年12月,列宁写道:
我们大俄罗斯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对民族自豪感是否有陌生的感觉呢?当然不是!我们爱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的国家,我们正在尽最大努力去提高她的劳苦大众(即十分之九的人口)的民主和社会主义觉悟水平。对我们来说,最痛苦的便是看见和感到,我们美丽的国家受到沙皇的屠夫、贵族和资本家的压迫和侮辱。令我们感到自豪的是,我们大俄罗斯人当中出现了抵抗些暴行的人,出现了拉季舍夫、十二月党人和七十年代的革命平民;而大俄罗斯工人阶级在1905年创建了一个强大的群众革命政党;同时大俄罗斯农民也开始转向民主,正著手推翻神职人员和地主......
...... 我们充满了民族自豪感,因为大俄罗斯民族创造了革命的阶级,它也已被证明是同样能够提供给人类为自由和社会主义斗争的伟大榜样,而不只是大烧杀、并列的绞刑架、地牢、大饥荒和对神父、沙皇、地主和资本家的无比奴性。
列宁就是这些文字的作者。把这篇文章理解为列宁向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作政治让步是不公平的。他的整个传记都证明了,他不屈不挠地反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然而,这篇文章显示出列宁尝试运用革命来影响劳动群众的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情绪,从而利用这些感情以达到革命目的,这反映出他的敏锐触觉,他感到不只是工人阶级里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他自己党内也一样。为了革命目的而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和使革命目的去适应民族主义之间,只有一条细小的分界线。一个作者试图传达的信息,和这个信息的意义是如何被理解,二者之间并没有确切的吻合线。当它传达到越来越多的听众时,这信息的政治质量的减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列宁可能是打算给大俄罗斯工人阶级的革命传统一个致敬,部份较落后的党内工人则可能会理解为这是在提升大俄罗斯人的革命能力。托洛茨基对列宁的提法提出批判是正当的。正如在1915时他写道:
只探讨在民族边界之内进行社会革命的前景,会同样成为民族狭隘性的牺牲品,因为它构成了社会爱国主义的实质内容。...... 总的来说,我们不应该忘记社会爱国主义和最庸俗的改良主义一样,它们都有一种民族革命的弥赛亚主义,认为自己的民族国家,无论是因为它的工业水平,或是因为其“民主”形式和革命的成就,被要求去带领人类走向社会主义或民主。如果革命的胜利在单独一个较发达的国家内成功是可设想的,则这弥赛亚主义与保卫本国的纲领,便可有些相对的历史合理性。但实际上这却是不可想象的。用这种方法去争取及保存一个以民族为基础的革命,便会破坏无产阶级之间的国际联系,并实际上破坏革命本身,因为革命可以在民族的基础上开始,但却不能在目前欧洲各国经济、军事和政治上相互依存的基础上完成,而这种相互依存性从来没有如此有力地显现在当前的战争中。
列宁重新评估自己政治观点的背景是值得研究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下他对世界经济的研究,使他对俄国革命的动态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促使他实质上采用了与托洛茨基相联多年的观点。
当列宁在1917年提出他的《四月提纲》时,在大厅里的人都理解到,他是沿着托洛茨基的路线提出论点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指控马上被提出,就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理解托洛茨基对当年革命成功的巨大思想贡献。托洛茨基已经为布尔什维克党内进行辩论提供了所需的思想和政治框架。但这并非是完全突如其来的事。如果以列宁的个性和他在布尔什维克党无可挑战的地位,能使新观点相对快地成功被接受,托洛茨基率先提出的不断革命论则促进了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斗争,尤其是在1917年,当俄国群众正向左转的情形下。
在某种意义上,1917年春夏秋三季所发生的不过是12年前所发生的一种形式。我想读出孟什维克西奥多 • 丹所写的书,名叫《布尔什维主义的起源》,其中一段有趣的章节。
他对1905年提出以下的看法:
我们看到了这“自由的日子”[1905年革命的高潮]的背景是,实际上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都被推向了“托洛茨基主义”。在一个短暂的时期里,托洛茨基主义(那时当然还没有这个名称)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成为了它统一的平台。
即是说在1905年,在俄国工人阶级转向左边的最爆炸性的时刻,托洛茨基的观点获得了巨大的威信和地位。这个过程在1917年得以重演。1917年的胜利验证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观。可是在1922-23年间反对十月革命的政治反动和俄罗斯民族主义最初复苏时,在政治上也表现为布尔什维克党内旧的反托洛茨基倾向再次冒出水面。我们不能认为当时的倾向与1917年时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政治分歧是无关的。但这并非意味着它们是完全一样的。
布尔什维主义在1917年的增长是基于各大城市中心的工人阶级的急剧激进化。但在1922年和1923年支撑党的增长的社会力量,却令列宁极为关注,因为在很大的程度上它包括了非无产阶级的成份,特别是来自城镇的中低层中产阶级,对他们而言革命开辟了无数的钻营升官的机会,更何况是那些旧沙皇官僚的残余份子。这些份子或多或少把俄国革命看作为仅仅是一个民族性的、而并非国际性的事件。早在1922年,列宁已开始警告这种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增长,对沙文主义倾向提出了日益尖锐的谴责。在1922年底和1923年初,这些警告尤其是针对斯大林,他在列宁的心目中已经成为了一种恶劣的社会形态,即“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恶霸”的化身。
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实质上是党内反对不断革命论的政治复苏。是什么阻止了托洛茨基去清楚地指明这一点呢?我认为答案在于列宁的病重和逝世造成的极其困难的情况。我估计托洛茨基觉得几乎不可能用他所渴望的率直去论述他本人曾与列宁有过的分歧。
这只有留给阿道夫 • 越飞在1927年11月,为抗议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共产党而自杀前几小时写的著名的信,他说经常听到列宁谈及在关于方向的根本问题上,对的是托洛茨基而不是他自己,这包括了不断革命论的问题。
托洛茨基当然觉察到党内领导层政治矛盾中的民族主义潜台词。在接近他的生命终点时,托洛茨基明确表示,苏联的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根源于1917年之前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分歧。他在1939年写道:“可以这样说,整个斯大林主义,就其理论层面上来说,都是出自对1905年所提出的不断革命论的批判。”
托洛茨基将继续以世界革命的理论家而在革命运动的意识中占有宏大的地位。当然,他比列宁活得更长,而且面对新的问题。但是,从1905年直到他在1940年逝世时,托洛茨基所有的工作都有其基本的连续性。为世界革命斗争的观点是他一切工作的决定性和实质性的主题。列宁的全部都包含在俄国革命中。但对托洛茨基而言,这只是他生命中的一个插曲——当然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插曲,却仍然只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更大剧本内的一个插曲。
回顾托洛茨基在他失去政治权力后的工作,会超出一个讲座的范围。但是,在结束这个演讲时,我想强调托洛茨基理论遗产的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他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最后一位伟大的代表。
在谈及经典马克思主义时,我们心里有两个基本的概念:第一,社会的基本革命力量是工人阶级;第二,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任务是要不知疲倦地,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去建立工人阶级的政治独立性。社会主义革命是这种持续和不妥协的工作的结果。工人阶级的政治独立是不能通过巧妙的策略达到的,而是在最根本的意义上,要通过教育——而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教育它的政治先锋队。捷径是不存在的。正如托洛茨基经常告诫说,革命战略的最大敌人便是缺乏耐心。
二十世纪见证了工人阶级最伟大的胜利和最悲惨的失败。我们必须吸取过去100年来的教训,而只有我们的运动开始了这项工作。在历史上,没有什么东西会被浪费或遗忘。国际工人阶级下一次伟大的斗争高潮——其国际规模已由资本主义生产的全球一体化所保证——将会见证托洛茨基主义,即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复兴。
* * *
1.本文是世界社会主义网站编辑部主席和美国社会主义平等党全国主席大卫·诺斯2001年1月21日在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平等党在悉尼主办的国际学校的演讲。这是演讲的修订文本,收录在大卫 • 诺斯的《捍卫列昂·托洛茨基》一书里。
2.Writings of Leon Trotsky 1939-40J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2001), P' 298.
3.Leon Trotsky, In Defence of Marxism (London: New Park Publications, 1971, p. 39.
4.Robert J. Alexander. International Trotskyism, 1929-1985: A Documented Analysis of the Movement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32.
5.Leon Trotsky, 1905 (New York: Vintage, 1971). pp. 459-460.
6.Ibid.. p. 356.
7.Leon Trotsky.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London: Pluto Press. 1977). P' 201.
8. Ibid..p.247.
9. Leon Trotsky, Terrorism and Communis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9,p.l8.
10. Leon Trotsky, Trotsky’s Diary in Exile, 1935 (New York: Atheneum, 1963, pp. 46-47.
11. Cited in: Writings of Leon Trotsky[1939-40].p. 57.
12. Leon Trotsky, Permanent Revolution (London: New Park), p. 240.
13. Leon Trotsky, "Our Differences," in 1905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1, pp.314-317.
14. Ibid., pp. 317-318.
15 V.I.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ume 21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4), pp. 103-104.
16 Cited in: Leon Trotsky,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After Lenin (London: New Park Publications, 1974, p. 51.
17 Theodore Dan, The Origins of Bolshevism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0), p.345.
18 Writings of Leon Trotsky[1939-1940],p. 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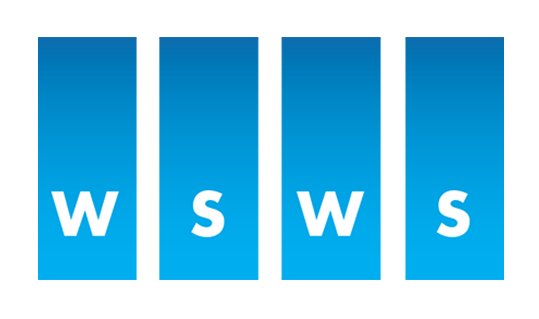
Follow the WSWS